可以说,2017年算是私募基金提速发展的一年,但也同样是私募基金逐步迈入监管和走向规范的一年。不可否认,在互联网金融市场下,即使私募基金的准入要求较为严苛,但围绕私募基金衍生的刑事犯罪也是此起彼伏,特别是非法集资的犯罪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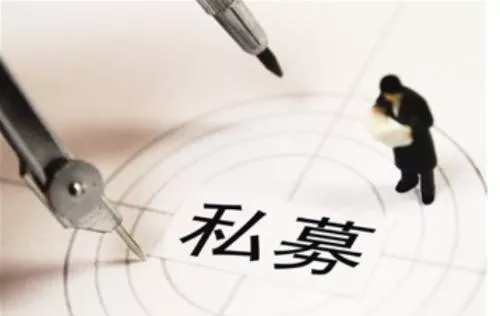
昨日,笔者就看到一则私募基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罪的典型案例。该案是一起利用未备案的私募基金募集从事房地产项目投资,募资达17亿元,到期未兑付6.7亿,而其中募集的资金仅1.1亿用于房地产项目,后经两审法院终审,被判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中公司实际负责人朱琦、市场部经理孙维晔、市场部专员郭晶三人分别领刑四年六个月、四年、三年六个月。结合这个案例,笔者跟大家谈谈私募基金如何演变成了非法集资,以及该案的类型认定、相关人员的地位认定与刑罚裁量等问题。

NO.1
一、 利用未备案的私募基金,开展募集资金活动,如何成了非法集资?
私募基金,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实现资金的大量募集,这也使其极易偏离合规募集的范畴,坠入非法集资的“雷区”。根据对私募基金募集过程中的行为予以分析就会发现,其涉及非法集资的风险点主要体现在募集主体、募集对象、募集方式等方面,再结合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是否触及非法集资,一般会从“四个特征”上来认定考量,该案的判决书,二审法院也就该公司及相关人员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从“四个特征”上予以了详细论述。
第一,主体非法性,即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根据判决书可见,该案中的私募基金未进行相关的备案登记,且公司实际负责人朱琦也未向投资人披露所募集资金的真正去向,所涉的上海天蔓公司等涉案相关公司没有存款业务的经营权,相应的融资行为也未依法履行相关融资法律程序,具有非法性特征
律师分析
私募基金,虽无须进行注册批准,但机构需进行登记,基金管理人及基金产品需进行备案,一旦所涉私募基金不予登记备案,而是径行开展募资工作或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极容易被认定为非法集资。另外,不管是在金融市场中,还是笔者实际接触过的一些非法集资案件,总有很多人认为,只要私募基金管理人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登记备案,那就可以放心开展募资工作,就不会涉及非法集资犯罪。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且存在很大的风险。
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之规定,向基金业协会所办理的登记备案,并不构成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能力、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也不作为对基金财产安全的保证。也就是说,登记备案并非进行实质性审查,不能以此作为合法吸收资金的决定性因素,其核心仍在于前述的募集对象是否不特定、募集方式是否公开,是否存在承诺保本付息行为。况且,在没有进行登记备案的情况下,就径行募集资金,其风险更大。
第二,社会性,即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根据该案的判决书可见,朱琦等人为了规避合伙制基金的人数限制,成立多家有限合伙企业吸收资金,即使从表面上看有的合伙企业的人数没有突破50人的人数限制,但实际吸收资金总的人数已远远超过人数上限。
律师分析
合格投资者制度是私募制度的核心内容。这一制度是因私募市场的高风险性决定的,是为了防止不能够承受风险的人或者不成熟的投资者进入,故基金募集的对象限制为具有特定资格的投资者。同时,并非有特定资格的投资者就可随意进入,相关法律规定还对合格投资者的人数有限制,就契约型基金而言,基金人数总共可以达到200人,而公司型和合伙型均不得超过50人(包含管理人在内)。
也正是如此,在通过私募基金进行资金募集时,很多人会想当然认为:“只要投资者的人数不突破50人或200人,即是合法合规的”,这一认识同样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
人数限制只是私募基金募集的原则性规定,并不代表未突破人数限制就一定属于合规私募。所以,人数限制属于对“特定对象”的一种范围限定,并不是界分风险有无的唯一性因素。正如该案中,虽表面上对人数限制这一条件没有突破,但是实际的资金来源人数则远远超过了这一限制,也反映其集资行为指向根本没有针对性,相反在募集对象的选择上具有普遍性。
第三,宣传公开性,即通过各种媒介向社会公开宣传。
该案的判处书针对“公开宣传”特征是如此论述的:该案投资人大多通过亲友、邻居、第三方中介的银行经理、理财公司业务员以及孙维晔、郭晶的介绍等“口口相传”的方式知晓上海天蔓公司吸收资金的信息而前来投资,这种口头宣传的方式通过上诉人、知情人、先行投资人对周围人员的广为传播,事实上在不特定人群中构成非法吸存信息的发散性传递,符合非法吸收资金的公开性特征。
律师分析
诚知,私募与公募有一个明显区分,那就在于公募是可以公开进行的,而私募则不允许。其实,公开宣传的具体途径可以多种多样,在相应的司法解释中也有所列举,但不应局限于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这几种。该案判决中提到,其公开宣传的方式是“口口相传”。
那“口口相传”的方式是否一定就符合公开宣传呢?答案并不是肯定的。“口口相传”虽是非法集资犯罪中的一个常见宣传方式,但并不是所有的“口口相传”都应被认定为“向社会公开宣传”。此外,向社会公开宣传系判定行为人主观上有无向社会不特定对象集资的客观依据之一,我们也可据此进行反向推测,如果“口口相传”的对象限定为单位内部员工之间,或者亲友之间,没有向外辐射,且行为人在事先、事中均有控制,或者在蔓延之际有设法加以阻止的,则很难认定其系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故而这种“口口相传”也难以认定为公开宣传的方式。
所以,对于以口头等方式发布、传播集资信息是否属于公开宣传,能否将“口口相传”的效果归责于集资行为人,应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结合行为人对此是否知情、态度如何、有无具体参与、是否设法加以阻止等主客观因素具体认定。”(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关于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二)》的规定)。
第四,利诱性,即承诺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或者给予报酬。
该案的判决书可见,投资人签订的认购合同、投资推介书等书证及投资人证言可以证实,朱琦、孙维晔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予投资人固定的回报,并向投资人承诺返本付息,且约定的回报远高于正常的存储或理财产品的收益,符合利诱性特征。
律师分析
关于“利诱性”,相较于其他三点,其实是比较容易认定的,因为这类还本付息的承诺或者变相承诺,基本都会落实到相应的行为人与投资人的文本之上,且在实践操作中,很少出现所有投资人均未拿到相应“利息”或“报酬”的情况,如此也可通过投资人证言,并结合相应的银行流水明细予以查证,证实的难度不大。
NO.2
二、 该案的犯罪类型、行为人的地位认定与刑罚裁量
其一,从该案的判决可以发现,该案被认定为单位犯罪。
当然,从整个判决书来看,各行为人通过涉案的上海天蔓公司开展私募基金,被认定为了被告单位。其实,在司法实务中,以单位犯罪驳自然人犯罪,是辩护律师常用的辩护点之一。根据相关解释及纪要对单位犯罪的认定,从正向和反向提供的标准来看,辩护时可主抓三个核心点:一是涉案公司的成立情况,包括成立目的与成立过程;二是涉案公司的业务构成,非法集资业务是否是其主营业务或单一业务;三是非法集资活动的开展情况,以单位名义实施还是以个人名义实施,以及违法所得的归属情况。当然,单位犯罪辩护的情形虽经常在法庭上出现,但实务中采纳率较低,这也是一个现实。
其二,行为人的责任与地位认定。
如前所述该案系单位犯罪,也就意味着除对单位有相应的惩处之外,还需对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
关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一般是指单位的领导人员,如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业务负责人等;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则一般为单位内部非领导成员,相关的认定标准,在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有所规定。
但笔者需要指出,在实务中,往往是在“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上,法、检与律师之间存在较大分歧。而上述所及规定,也只是概括性描述,很难据此明确评断涉案人员的地位认定。笔者认为,这个时候就要详细考查行为人的实际工作性质,他在整个非法集资犯罪链条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光盯着行为人的职称身份,称谓只是身份的赋予,而确定其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以及需要承担多大责任,则要着重分析其客观上的行为属性、职责分工、行为程度等。
其三,关于该案的刑罚裁量。
从该案的二审判决结果来看,二审法院实则做了相应的“从宽轻判”。可以发现的是,在案件事实认定以及行为性质认定上均无更正,那“从宽轻判”的理由来自何处?那就是在二审期间,朱琦等人存在积极筹划还款,其中有代为退缴的部分资金1.1亿元,划至法院账户,并且促使债权人放弃了对A公司的1.8亿元的债权,在客观上增加了本案被害人的清偿比率,为投资人挽回部分损失。可见,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集资案件中,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固然是重要的,但是追回并尽力弥补投资人的利益损失,也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如果在案发后,行为人能够有相应的减损(如积极退赃或者提供涉案赃款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查扣涉案赃款),那在最终的刑罚裁量上,相较于无法挽回损失的案件情形,会有一个相对明显的“从宽”体现。


